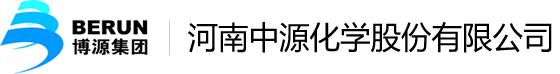
Henan Zhongyuan Chemical Co., Ltd.
2025-09-26 15:26:33 文/马本兵 字数:517
九月的雨,像被谁扯破的棉絮,没完没了地往下落。田里的花生早已成熟,却泡在泥水里,等着人们去收。
父亲蹲在地头,捏起一把湿土,轻轻一攥,土便从指缝里滑落,像流沙。“再等两天吧,”他抬头望天,雨丝斜斜地打在脸上,“收了也晒不干。”
可花生等不得。雨泡久了,荚果会烂在地里,一年的辛苦就打了水漂。母亲翻出雨衣和胶鞋,又找出几个旧麻袋,塞进拖拉机的后斗。“总得试试。”她说话时,雨声淹没了尾音。
我们踩着泥泞下地。花生藤被雨水浸得发黑,一拔就断,泥土黏在根须上,沉甸甸的。妹妹的手被划出几道红痕,却还固执地拽着藤蔓:“妈,这棵肯定结得多!”雨水顺着她的刘海滴进眼睛里,她眨眨眼,又笑了。
拖拉机陷进泥坑的那天,雨下得更急了。父亲和邻居老李喊着号子推车,车轮碾过的地方,溅起一片泥浆。老李抹了把脸,说:“这雨,跟老天爷哭丧似的。”母亲却把麻袋往车上一甩:“哭啥?花生收一点是一点。”
傍晚,我们拖着半车湿花生回家。灶房里,父亲烧起柴火,把花生摊在铁网上烘烤。火苗噼啪作响,烟混着雨气从窗缝钻进来。妹妹趴在灶台边,捡起一颗烤得微焦的花生塞进嘴里:“真香!”
雨还在下,但屋里暖烘烘的。花生壳上的水珠渐渐蒸发,像一场无声的告别。